重生之路:珍尼湖的生态觉醒

2025年9月4日,在马来西亚彭亨州珍尼湖生物圈保护区丹戎普特村,一名贾昆女子牵着孩子
文/《环球》杂志记者 王嘉伟 谭耀明 毛鹏飞(发自吉隆坡)
编辑/马琼
马来半岛彭亨州中南部群山环抱的珍尼湖,曾经满湖荷花、碧绿如镜,承载着多样的水域生态与独特的文化记忆。然而,这颗“绿宝石”在人类开采、农垦与开发的重压下曾一度走向衰退,又在研究者、原住民与政府的共同守护中重焕生机。
作为马来西亚首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人与生物圈共生的理念在珍尼湖治理与保护过程中被不断具象化:生态治理不再只是技术工程,也不是单一部门的任务,而是科学监测、政府施策与社区文化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
昔日盛景难寻
珍尼湖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天然淡水湖,由12个形态各异的湖盆组成,总面积超过6900公顷。2009年,凭借其山水相依的自然景观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珍尼湖被认定为马来西亚首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
马来西亚媒体《星洲日报》曾撰文记录珍尼湖的昔日盛景:每年7月到次年1月,粉红与白色相间的荷花铺满湖面,只留下一条水道供船只穿行,景色迷人。“可惜那些关于船只驶入花丛、清淡花香迎面扑鼻的盛况,如今仅剩下海报上的照片,长存于历史的记忆中。”
“以前珍尼湖的森林和湖泊是最完整的,野生动物也很多。”年近七旬的巴哈林回忆说,“年轻时,划船出湖要先用竹竿拨弄开荷叶,船只才能穿行;后来湖水逐渐变浅变浊,鱼类越来越少,莲花花期也不如往昔。”
巴哈林是珍尼湖边密林中的贾昆族原住民村的村长。对于世代在此繁衍生息的贾昆族而言,珍尼湖不仅是家园,更是族群传说与精神寄托的中心。至今,长者仍会娓娓道来有关湖底巨龙的神话——湖底沉睡着一座黄金满堂的高棉古城,由巨龙守护以阻止贪婪者染指宝藏。
珍尼湖生态衰退的轨迹可追溯至十多年前的资源开发浪潮。“随着2010年矿产资源价格上涨,周边地区矿产开采等工商业活动越发频繁,对珍尼湖周边生态造成严重破坏。”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珍尼湖研究中心研究员努尔·阿梅莉亚·阿巴斯说。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珍尼湖上游河流堰水大坝建设的推进,周边采矿与伐木垦植活动不断扩张,这片原本偏僻的山区被快速纳入资本版图。
长期无节制的采矿、农垦扩张和监管不足的旅游开发,使珍尼湖的生态持续退化——湖水浑浊、生物减少,周边山丘伤痕累累。“荷花原本依赖自然水位涨落而生长,但失去稳定的水深与水质环境后,昔日满湖盛放的景象便逐渐消失。”阿梅莉亚说。
生态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该地区曾记录有约80种鱼类,后来只剩下20多种。此外,湖水水位异常波动、水质检测持续下滑、环保团体公开警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珍尼湖亮出“黄牌”提醒……勾勒出这片湖泊复杂而紧绷的现实图景。
马来西亚生态学家曾直言,珍尼湖水质若进一步恶化则可能导致岸边植被大面积死亡并沉入湖底,进一步加剧沉淀累积,导致水体更加浑浊。“再不做些什么,珍尼湖将因干涸彻底消失在地图上。”

这是2025年9月4日在马来西亚彭亨州拍摄的珍尼湖生物圈保护区景色
正缓慢复原
如今,珍尼湖湖水的颜色逐渐变好,水生动物栖息环境也在慢慢恢复。
但这并非能一蹴而就。早年筹备、申报并最终让珍尼湖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获批生物圈保护区认定,成为珍妮湖命运转折的关键。
“人与生物圈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1年发起的一项政府间大型科学计划。该计划提出一种新型自然保护理念,即设立生物圈保护区,把保护区及周边地区人民的生活改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找出一条既能保护自然、文化资源,又能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马来西亚不像瑞典或芬兰那样拥有成千上万的天然湖泊,我们只有两个,珍尼湖便是其中之一。”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名誉教授、珍尼湖研究中心创立人之一穆什丽法·伊德里斯说。正因如此,马来西亚的植物学家、生态学家、水文专家和技术人员齐聚一堂,思考“必须为它做点什么”。
申报团队系统搜集湖泊生态、森林、水文等资料,走访沿湖村落征得原住民支持。最终,一份厚重的申报报告呈交给政府,再递交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过程耗时整整两年。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使得珍尼湖备受瞩目,但这份沉甸甸的认可也迅速暴露了珍尼湖长期积累的治理短板:保护区分区界限模糊、开发边界难以落实、执法力量薄弱,管理制度一度难以支撑“生物圈保护区”的高标准……随着水质恶化、鱼类减少、荷花消失等迹象不断累积,政府、科研机构与原住民社区逐渐意识到:珍尼湖已进入“必须合力守护”的阶段。
随后的几年,湖区采矿活动被陆续叫停,退化山坡被纳入再造林范围,采伐许可被严格收紧,部分区域被重新划入全面保护区;彭亨州公园管理局等机构相继成立,使原本碎片化的治理架构逐渐形成体系。
湖区的生态修复亦随即全面展开。彭亨州林业局推出“买回造林”计划,由贾昆族原住民负责培育本地树苗,再由政府出资回购,用于填补裸露矿坑与受侵蚀山体。
水体与水域生态治理则复杂得多。据阿梅莉亚介绍,研究团队从流域入手,通过在坡地铺设覆盖作物、在河岸采用椰纤圆木带稳定土壤,减少雨季里泥沙直冲湖面;在废弃矿区引入微生物与堆肥技术改良贫瘠土壤,为植被恢复创造条件。“我们还组织了多轮社区协作,清除曾大面积扩张的外来水生植物,让本地水草重新获得生长空间。”
在湖面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用于荷花复育的试验浮台,这也是珍妮湖研究中心助理工程师伊克万投入较多精力的地方。“荷花复育很难。”他说,“以往湖水季节性起落促使根系萌发,但上游水坝改变水位节奏,我们需要不断试验,探寻适宜荷花繁育的方法。”
伊克万介绍,荷花复育工作得到了马来西亚政府和森林研究院的双重助力。研究团队先在陆地上育苗,再将其移至浮台,最后让荷花重返原本的自然栖息地。
如今,从试验浮台上重新绽放的荷花,到山坡上抽芽成林的幼树,再到河岸湿地植物重新返场……每一个迹象都在表明,这片湖泊正在从创伤中缓慢复原。
“它的问题具有全球性”
珍尼湖在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中的重要地位,并非因为其广阔的面积,而在于它承载着生态、经济、文化等多重压力。珍尼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认为,珍尼湖的治理经验,为全球众多面临多方博弈的保护区探索出了一些好的方法。
在“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理念下,治理不是自上而下单向度的安排,而是由多方共同承担。“珍尼湖修复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如何让政府、科研人员和社区真正成为共同治理的伙伴。”彭亨州公园管理局首席执行官扎伊纳尔说,公园管理局经常讨论,如何将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原住民社区及非政府组织的声音纳入治理框架,“这种跨部门与社区的频繁互动,正是未来珍尼湖继续走向复苏的关键。”
最近两年,一些国家的研究者也来到珍尼湖考察,学习如何处理产业活动、湖泊治理与社区发展叠加压力情况下的治理难题。“珍尼湖面积不大,但它的问题具有全球性。”扎伊纳尔说,“这正是它的独特之处。”
珍尼湖的故事也正在被更多人听见。在2025年9月于杭州举办的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上,珍妮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穆什丽法分享了热带湖泊治理与社区参与经验。“珍尼湖作为生物圈保护区已走过16年,即将迎来新的评估周期。希望借鉴中国同行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保护实践,留下更完整的修复记录,把经验传递给下一代。”
对贾昆族原住民而言,他们的期待则更具体。巴哈林坐在高脚屋前,望着傍晚的湖面,“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孙辈划船驶向湖心时,能再次看到满湖荷花的样子。那样的话,我们这些老人就可以放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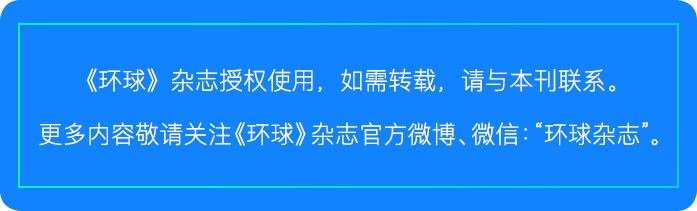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